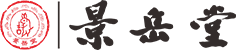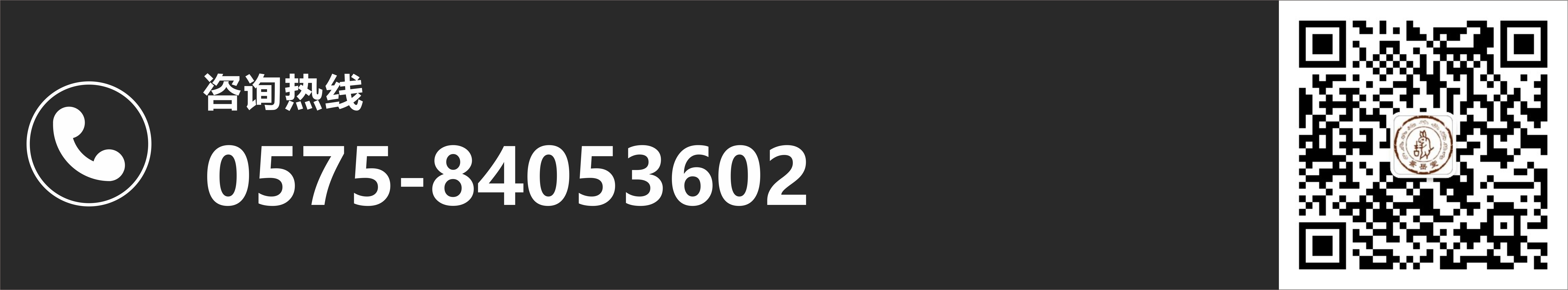(1563-1640),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汉族,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13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张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仲景东垣再生。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78岁。
推崇丹溪之学
张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年-1558年),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著书立说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 于天启四年(1624年)。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学术贡献
《景岳全书》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辨,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后世叶桂亦多承张氏的理论。清道光八年(1828年)章楠《医门棒喝》初集成,论《全书》云:“或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则自顺治中叶至1828年的近200年间,几为医所必读,可见景岳的温补理论之影响深远,《全书》之流传广泛。
《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内经》的较好参考书,《景岳全书》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张景岳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对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医学思想
在整个中医理论发展史中,张景岳的医学思想体系居有重要地位,代表着中医理论的新的发展阶段。他的以温补为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进步和完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进一步完善了气一元论,补充并发展了阳不足论,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火命门说,对后世养生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景岳医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与宋明理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理学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形态中最具哲学性的思想体系,集儒释道三家于一身的理学构建了新的以“太极”为核心、理气相随的哲学形态,吸收了当时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成果,被誉为中国本土的有机自然主义萌芽。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深深植根于理学思想之上,运用理学家的观念对《黄帝内经》作了全新的诠释,著有《类经》等书,并成为后世医家学习和研究《内经》的范本,故研究其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有利于对整个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状况进行宏观把握。 本文从医学思想的转型与理学思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以张景岳医学思想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温补思想为切入点,通过对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朱熹等理学大家的哲学思想对张氏思想体系形成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全面系统的总结出张氏医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景岳全书》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成书于其卒年1640年。“《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全书·传忠禄》辑有景岳主要医学理论、医评、问诊和诊断、治疗原则等论文三十余篇,多有温补学说的论述。《全书·脉神章》录有历代脉学,其中诊脉之法和脉象主病多有结合临症经验的评论。次为《全书·伤寒典》,补充“《内经》伤寒诸义并诸治法之未备”,论述伤寒病的证治。《全书·杂证谟》列诸内科杂证的病因病机、治理方药和部分医评,并辅有部分医案,论述系统、精采。《全书·妇人规》:论述九类妇科疾患,并指出妇科证多有情志病因,尤要注重四诊合参。《全书·小儿则》:更述儿科诸病并治,在总论中提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生理特点,很有见地。《全书·痘疹铨》、《全书·外科钤》各有论病及证治。《全书·本草正》介绍药物二百九十二种,每味详解气味性用,很多为自己的临症用药体会,颇有价值。《全书·新方八阵》、《全书·古方八阵》,景岳善兵法,在此借用药如用兵之义,以方药列八阵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全书·新方八阵》中所列方颇具创新。《全书·古方八阵》辑方经典。共录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其后的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古方收妇科186方,儿科199方,痘疹17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种。
用药特色
1、临证用药 精专简炼张景岳处方用药,讲求“精专”二字,从不鱼目混珠,庞杂为用。这一特点在新方八阵中体现得最为明了,淋漓尽致。张景岳认为:“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故其首先大力提倡药力专一。他的自创诸方,药力均纯厚精专。如“补阵”中的左归饮、右归饮、左归丸、右归丸,皆由古方变通而得。此四方均去原方之泻,增培本之补,使其纯补而不杂,药专而有力。集中体现了张景岳“与其制补以消,熟若少用纯补”及“若用治不精,则补不可以治虚,攻不可以去邪”的用药思想。
其次,张景岳还力倡处方用药药味宜精。药杂味多,则药力必不能专。故药味精简,是景岳处方用药的又一大明显特色。据统计新方八阵计186方,每方药物超过10味的仅见13方,约占总方的7%;用药数以6~8味居多,共88方,约占47%;而5味药以下者共有58方,约占31%。平均用药,每方约6味。由此可见,景岳用药确如其言,药力精专,简便兼验。
活用古方
景岳的许多自创新方,乃在推陈出新基础上别出新途,活用古方并补前人之未备而成。景岳化裁古方妙在不落古人窠臼,而能自出新意。以古方为基础,执古方“意贵圆通”之意,创立了很多新方,临床试用,效果甚显。如六味地黄丸本为补肝滋肾养阴之通剂,景岳以此为基础,举一反三,衍化出5首类方。大补元煎即六味地黄丸中增入人参、归,即变滋阴养肾之方为大补气血之剂;左归饮即六味地黄丸加枸杞、甘草,改治肾阴不足,腰酸遗泄,舌红脉细;右归饮即六味地黄丸加杜仲、附子、肉桂、枸杞,用治肾阳不足,命门火衰,气怯神疲,肢冷脉细;左归丸即六味地黄丸加菟丝子、牛膝、龟板胶等而成滋补肾阴,填精益髓之剂;右归丸即六味地黄丸加附子、肉桂、当归等而成温补肾阳,用治命门火衰之方。
以上衍化新方均不离治肾培元之宗旨,以此为基础,或兼以温补气血,或兼以培补肾阳,或兼以滋肾养阴,或兼以填精补血。由此可见,景岳对六味地黄丸的加减化裁,临证应用已达到运用自如之境地。至于对其它古方的变通应用,借此六味地黄丸一例,已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长于温补
景岳十分重视人体正虚为病,基于“阳非有余,阴亦不足”之说,大倡扶正补虚之理。景岳用补,先以形体为主,注重温补精血。他在“八阵”中讲到:“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大门路也。”景岳所言形者即阴之谓也,故又有“形以阴言,实惟精血二字足以尽之”的论述。
试观新方八阵,景岳常用的补精血药物有熟地黄、当归、枸杞等味。其中则以熟地黄为首选之品。景岳曾云:“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至静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成中第一纯厚之药。”新方八阵用熟地黄者计47方,占总方之25%左右。而补阵29方,用熟地黄者21方,约占72%。景岳用熟地黄填补精血,所治病患极广,诸如外感表证、呕吐、水气、肿胀等等,此均为历代医家用熟地黄有所避忌者。景岳则不拘常法,信手拈来,屡收奇效。
其次,景岳用补的另一特色即是补必兼温。景岳曾云:“虚实之治,大抵实能受寒,虚能受热,所以补必兼温,泻必兼凉。”故于临证之际,凡扶正补虚者,景岳多以温补为主旨,其善以附子、肉桂、干姜、人参等药为温补之用,而其变化出入使用上,诸药在新方八阵中则比比皆是。
景岳长于温补,于当时,实乃救误应时之所为。景岳曾说,自金元以来,河间刘守真创“诸病皆属于火”之论,丹溪朱震亨立“阳有余而阴不足”之说,后人拘守此说,不论虚实,寒凉攻伐,此均为力救其偏之治。他认为“凉为秋气,阴主杀也,万物逢之,便无生长,欲补元气,故非所宜。凉且不利于外,寒者益可知矣。”并宗《内经》“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之论,力倡温补而终成一家之言。
民间传说
张景岳是明代著名医学家,人们都知道他善用温补,却很少知道他还有一段急智解危的故事。
一户姓王的人家有个儿子,刚满一岁。一日,母亲随手拿一枚钉鞋的圆铁钉给儿子玩。小孩不知,误塞入口中,吞到喉间出不来。其母见状大惊,忙倒提小孩两足,欲倒出铁钉,哪知小孩反而鼻孔喷血,情况十分危急。孩子的父母连呼救命。恰好张景岳路过这里,他见状急命其母将小儿抱正,小儿“哇”地一声哭开了。景岳断定铁钉已入肠胃,小儿父母早吓得六神无主,迭声哀求张景岳想想办法。
张景岳陷入沉思中,他记起《神农本草经》上有“铁畏朴硝”一句话,想出一个治疗方案。他取来活磁石一钱,朴硝二钱,研为细末,然后用熟猪油、蜂蜜调好,让小儿服下。不久,小儿解下一物,大如芋子,润滑无棱,药物护其表面,拨开一看,里面正包裹着误吞下的那枚铁钉。小儿父母感激不已,请教其中的奥秘。
张景岳解释说:使用的芒硝、磁石、猪油、蜜糖四药,互有联系,缺一不可。芒硝若没有吸铁的磁石就不能跗在铁钉上;磁石若没有泻下的芒硝就不能逐出铁钉。猪油与蜂蜜主要在润滑肠道,使铁钉易于排出——蜂蜜还是小儿喜欢吃的调味剂。以上四药同功合力,裹护铁钉从肠道中排出来。
小儿父母听完这番话,若有所悟地说:“有道理!难怪中医用药讲究配伍,原来各味药在方剂中各自起着重要作用哩!”
学术思想
“中年求复,再振元气”是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关于我国中老年医学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对其所提的“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中年求复,贵在复元惜元的思想和重要意义,以倡其中兴延寿之旨。
深远意义
人所具有的天然寿命,古人称之为“天年”,认为是与先天元气相关。当然,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且往往取决于元气强弱。从这一角度言,显然人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故张氏《景岳全书》云:“此人之制命于天也”。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能尽其天年,这与后天是否很好地调摄养生有很大关系:先天虽强,不加惜护,仍可夭折;而先天虽弱,但勤于慎节,有时反得长寿。首先,张氏并非唯先天论者,他也非常强调后天的作用。正如他在《先天后天论》中所说:“后天培养者寿者更寿,后天祈削者夭者更夭”;“若以人之作用(后天)而言,则先天之强者不可恃,恃则并失其强矣;先天之弱者当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在《中兴论》中也指出:“若后天之道,则参赞有权,人力居多矣。”从这一角度言,人对自己的寿命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某些主动权。故张氏又云:“此天之制命于人也”。通过这样的分析,张氏突出了人在掌握自身寿命上的能动作用,得出了“后天之养,其为在人”的结论,确是有其说服力的。
由盛而衰期
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我国古代对此早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且认为女子七七而男子八八则天癸竭,即标志着人体由此逐步进入了老年期,已可出现早衰和种种老年病。《备急千金要方》所谓“四十以上.即顿觉气力一时衰退;衰退既至,众病蜂起,久而不治,遂至不救”。面对早衰现象和渐入老年,前贤反复强调了摄生的重要意义,认为决不可在衰老之后再重保养。因为衰老之体,元气大虚,精血枯竭,脏腑亏弱,欲求复壮、延年,其亦难矣。这也就是古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经旨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但是,张氏并未停留于此。他进一步对预防早衰作了重要的探讨,并鲜明地提出了“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卓越思想。预防早衰思想
张氏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从他的后天保养的观点出发,发挥了预防早衰的思想。他指出了早衰的产生是由于不知摄生,耗损精气,所谓“残伤有因,唯人自作”(《景岳全书》)。既然“所丧由人,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说明通过努力可能挽回早衰。因为,,人的生命过程是有规律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经历着生长壮老,故早衰使之复常才是遵循了生命的规律。在这一意义上,他强调了挽回早衰,此时所作,并“非逆天以强求,亦不过复吾之固有”(《中兴论》),何乐而不为也,甚至他在论中还满怀信心地说到:“国远皆有中兴,人道岂无再振?这里的关键在于元气,早衰即是元气大伤的表现。而挽回早衰,即在重振元气。”这就是“求复之道,……总在元气”。说明了应当抓住中年时期元气尚未大虚之机,认真地加以调理,使元气得以复常,而人身之根本得固。若以天年为百岁而言,中年时期的元气,难道不是还应该保持着大部分吗?我们不难看到,张氏的“求复”之论,遥接了《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不懂得运用阴阳和调这一养生规律,“则早衰之节也”;’倘能掌握养生之道,即可“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所以,张氏的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观点,是对该节经义的重大发挥。由于他的预防早衰的思想是基于对人体生命过程的深入了解,基于对中年期具有重要性的正确认识,因之不仅富于一种积极的主动精神,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科学依据。
许多老年性疾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中年后逐渐演变而成的。中年时期虽然在生理上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过渡时期,但其生理特点毕竟完全不同于老年时期,即使逐渐出现一些衰弱的表现,但却远比60岁或64岁以上的老人要气血旺盛、脏腑充盈得多,是故张氏力主“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然再振根基,尚余强半”(《中兴论》),加强调养,对于避免早衰,预防老年病等,无疑具有极大的意义,以尽享天年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情况表明,在300多年前张氏提出的中年求复的思想,确是十分可贵的。
惜元复元
爱惜元气防范未然《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人生在世,可“度百岁乃去”。可见当时己发现人的自然寿命在百余岁。据《尚书·洪范》解释,,“一曰寿,百二十岁也。”则更明确地
指出寿命的极限为120岁。张氏在《中兴论》中亦认定人之天年在百余岁。即使人的个体寿命因遗传差异而有所不同,虽不可能春秋皆度百岁,但绝大多数人是应该达到90以上至100余岁的。然而,事实上却是大多数人半百而动作皆衰,就其缘由,理当责之后天失养、元气受损。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人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恃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常,故半百而衰也”。张氏亦持此见,认为除天灾人祸等客观原因外,乃是“唯人自憎”(《中兴论》)。既然是“所伤由人”,则“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中兴论》)。元气乃人身根本,且在体内不能永存。人至中年,元气则由鼎盛而渐衰,因而对之更当惜之再惜。但总有人不明此理,“既已失之,而终不知其所以失也”。整日仍忱于酒、色、财、气、功名之中,以至“坐失机宜,变生倏忽”,令元气早衰。故张氏历陈其损元折寿之害,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惜元避害之法,曰:酒杀可避,吾能不醉也;色杀可避,吾能不迷也:财杀可避,吾能不贪也;气杀可避,吾能看破不认真也;功名之杀可避,吾能素其形藏也。”(《景岳全书·传忠录·天年论》),张氏这种既正视人的生理和社会需求,同时又提出应当对这些需求有所节制的思想,较之一味勉强无为和压抑人的正当需求的思想来说,无论从认识方面或实践方面均大有进步。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养生学,而且还为处于社会激烈竞争前沿的中年人如何去惜元保元,顺利步入健康的老年时期,以及对中年心身医学的研究,都提供了正确的思路。